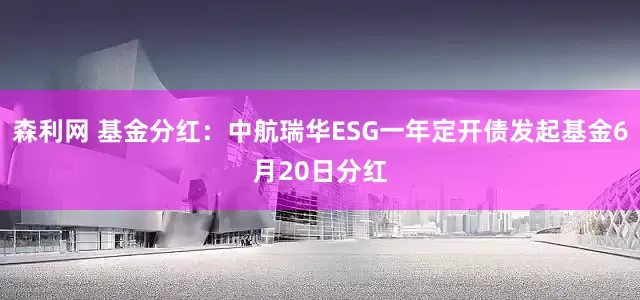【导读】6月21日,文汇讲堂176-4“全球南方在文明交流中共振与互鉴”的圆桌环节中,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作为主持,与上海市区域国别学会会长姜锋、该校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顾力行(Steve J. Kulich)和巴基斯坦国际文化遗产管理委员会成员纳西姆·汗(Nasim Khan)就文明互鉴与文化自觉间的张力、全球南方可否获得共同身份展开讨论,上篇以《淡水鱼能存活于海水里吗?人均有文化适应力》刊发,下篇四位学者聚焦区域国别学如何助力文明互鉴。
本期讲座内容整理有主讲上下、圆桌上下、提问、快评等,敬请关注。
 上海外国语大学现场
上海外国语大学现场
杨成:刚刚我在主报告的最后简要提及了区域国别学。姜会长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实践者和引领者,想向您请教,区域国别学在文明互鉴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区域国别学为新时代产物,是给我们的世界观补课
姜锋:从比较视角看,他文化或他者就是镜子,能照出我们自己,如同家长教育孩子会说别人家的小孩怎么好来起到榜样激励一样,他者当然也有好有坏。区域国别研究就是试图了解别的国家,了解别的区域。
从文明的维度看,“全球南方”国家越来越有自觉的意识,即他们在国际上越来越独立,越来越有自主的力量。过去我们了解了美国就能知道西方,知道了德国、法国就能了解欧洲,通过欧洲就可以了解到“全球南方”。现在不是了,绕道了解这个世界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全球南方”这些国家。区域国别学或区域国别的知识就诞生在这样的新的时代,我们等于是在补课,在给我们的世界观补课。不然,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与他国共同推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如何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因此,区域国别学或区域国别研究本身,尤其是在文明互鉴这个问题上,使命重大。
*“害羞”金牛股,玄奘记录里是“我很尊重你”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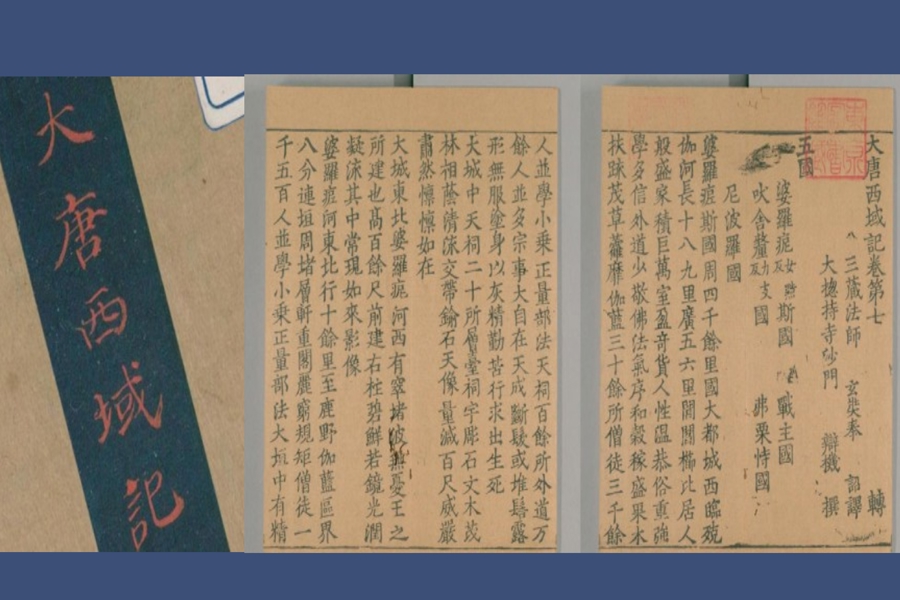 玄奘《大唐西域记》被姜锋称为典型的区域国别研究 来自书格网
玄奘《大唐西域记》被姜锋称为典型的区域国别研究 来自书格网
Nasim Khan:您说得太棒了,区域国别学里也有巴基斯坦的知识。我非常惊讶,许多中国的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等研究机构,不仅是教育机构还有个人,他们都会去做现场研究,甚至在学乌尔都语、普什图语和阿富汗的其它当地的语言,还不仅仅在巴基斯坦。让我更惊讶的是,现在许多年轻的中国人,竟然去开展各种不同的研究,且极有动力,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包括发表许多文章。在此之前,古犍陀罗地区有不少负面评价,但中国学者们带来全新的视角,让人们重新看待该地区。这个例子就是说明因为亲眼所见、亲自行走、亲口所食,所以很了解当地人。尤其我看到,中国学者逐渐更加自如地体验当地文化。
他者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当你评价一个人非常害羞,我的学生说这是一个负面的词,表示怯懦。我就举玄奘书中所说,在这个地区如果说害羞,意思是我非常尊重你。所以区域研究、国别研究、语言研究的重要性就在于此!它有助于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和平。
姜锋:非常感谢Nasim Khan教授,我此前曾说过,玄奘《大唐西域记》是一份很典型的区域国别报告。
*询问ChatGPT,问完哈佛教授再问肯尼亚人
杨成:非常感谢Nasim Khan关于玄奘故事的分享,这是他非常擅长的领域,他在犍陀罗艺术史上是世界知名顶级专家。美国在1947年到1953年创建Area Studies(区域学)时提出了跨学科、全覆盖和文化相对主义三个原则,显然是接受了人类学家的呼吁。因此理论上,美国将自己与其他民族、其他文明视为平等。但美国最初设定的目标显然没有实现。请问顾教授,西方的Area Studies很大程度上更紧密地与权力联系在一起,而非为文明互鉴服务,这样的现象是如何发生的?
 主讲后,主持人顾文俊请四位学者用不同语言翻译“美美与共”16字,图为顾力行用英文翻译,姜锋用德文,纳西姆·汗用乌尔都语,杨成用俄语与吉尔吉斯语
主讲后,主持人顾文俊请四位学者用不同语言翻译“美美与共”16字,图为顾力行用英文翻译,姜锋用德文,纳西姆·汗用乌尔都语,杨成用俄语与吉尔吉斯语
Steve J.Kulich:我毕业于汉学研究,中国研究、日本研究是我的主业,我也做跨中美德文化的研究。我涉猎领域较多,最早做科学研究,后做亚洲研究,接着是跨文化研究和人类学研究。区域国别研究金牛股,从跨文化的角度看有两个需求。首先必须了解每个国家区域研究都服务于该国政府的政治意识形态,因为资金都来源于政府。所以当学习了中国学来到中国后,我意识到自己有点问题,因为我的研究应该是中国想要什么,而不是美国想要听什么。我不想通过美国角度学习中国,我希望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当我用ChatGPT的时候,最早会关注哈佛教授或者斯坦福教授会如何教这个问题。现在我会问肯尼亚的学生、老师如何说这个事,尼日利亚如何看待此事,巴基斯坦的人碰到这个问题是何态度,让ChatGPT帮助我跳出自己的思维框架来考虑问题。我们希望建立全球的互动范式。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说,中国跨国企业在“一带一路”中的作为等,都是我们在研究的内容。
回到今天的主题——文明互鉴,每一种文化都有非常有价值的角度。我从捷克移民到德国,38年前与德国人结婚,每一个人都需要了解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观点。一个好词在另一种文化里,可能被翻译成非常浅薄的意思,如果有更多的眼睛观察,那这个信息就更加全面,更加丰富。所以,“将心比心”“美美与共”非常重要。我们必须了解几方和各方,这叫做“有意义的相互性”。我们必须分享,不仅仅出于学术考量,而且必须进行所谓的文化谦逊,考虑到互补性。
区域研究太过关注权力,即使所谓的软实力,也会令其他人和国家害怕。
第二个需求就是进行国别研究,国家内部也要进行多元化对话,这也非常关键。
*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核心是文明互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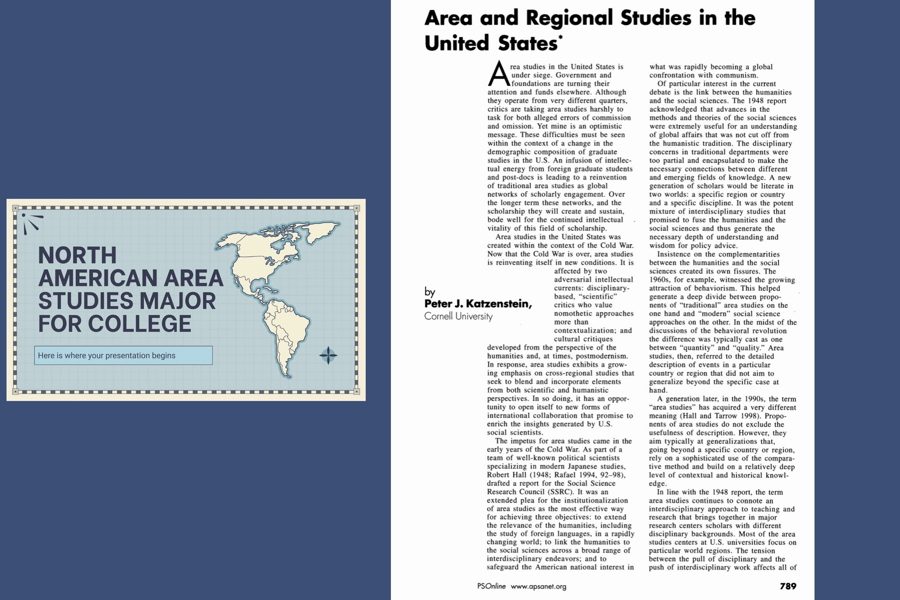 美国在1947年到1953年创建Area Studies的初衷与其后实践不同
美国在1947年到1953年创建Area Studies的初衷与其后实践不同
杨成:区域国别学不可能和权力毫无关联,顾力行教授所担心的在西方比较常见。请教姜会长,我们怎样才能保证既和国家利益相关,又大力促进文明互鉴,最后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姜锋:中国区域国别学在设计时就与欧美不同, 所以,没有用Area Studies,而是用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欧美区域学历史上起源于殖民、扩张和地缘政治对抗的需要,它要了解对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情况,目地是为了对付对方、统治被殖民国家。中国区域国别学则不同,了解对方是为了更有效交流与合作,文明互鉴是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的核心内容。中国区域国别学是补课的,我们在全球不断的互动中发现,我们对很多国家和区域其实并不了解,比如邻近我们的中亚地区等;对全球南方中的很多国家,我们了解很少。不了解对方如何合作?共同的文明互动、经济发展或政治互信,都需要知识的基础。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本质上是开放而相互促进的。
 2023年举办的慕尼黑安全会议
2023年举办的慕尼黑安全会议
前年我去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会上各方大谈全球南方的概念。有一场讨论,台上坐的是肯尼亚外长和巴基斯坦前外长,她们说,北方国家都在讲全球南方,如果你们只是想教育我们,想告诉我们应该走什么发展道路的话,那你们就错了,全球南方的人更关心要喝到干净的水,有好的医疗,孩子们要上学,你们能帮我们做到这些吗?
一位德国女士分享了去非洲的经历,她很有自我批评意识地说道,非洲人告诉她:你们欧洲人与我们谈发展,就是给我们上一堂民主课。中国人与我们谈合作,是商量建飞机场、港口、铁路。你们欧洲人能不能做点具体的?
肯尼亚前外长有一个观点让我印象特别深。她说,现在最担心的是发达国家搞地缘政治分裂,为了你们的权力斗争来争夺我们全球南方,这是最糟糕的,这是全球南方最不需要的。她的担忧有道理,慕尼黑会议上,欧美国家就是把全球南方看做与所谓的东方开展地缘政治争斗的发码。
为什么刚才突然想起这句话?我们在讨论全球南方的时候,也是一分为三或者一分为四,设身处地从我们谈的对象来考虑问题,这是区域国别研究、区域国别学非常重要的内容。
*全球南方呼声:不想再做“工具人”
 杨成主讲时,三位嘉宾听得全神贯注
杨成主讲时,三位嘉宾听得全神贯注
杨成:感谢姜会长特别精彩的分享。实际上,“全球南方”国家从来不想被大国分而治之,从来不愿只做大国地缘政治的工具,这种意识已经从文化觉醒上升到文化自觉,其背后是不断增长的主体性。无论是从事区域国别研究还是跨文化交际研究,我们都需要尊重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形成多主体之间的对话、合作。当我们将这样一种问题意识放置到区域国别研究的应用场景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不是一个宏大的目标,而是可以分解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前不久在中亚举行的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的成功举办足以证明,中国正在为中亚五国提供公共产品而非谋私利,没有把他们当作工具人,不是让五国帮助我们对抗美国或者其他被想象的竞争对手。中亚国家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一机制,高度评价这一机制,最关键的点在于他们得到了充分尊重,这恰恰符合了文明对话、文明互鉴的要义——承认彼此主体性,通过跨文化交际架起桥梁,最终形成利益之间的互嵌,在结构性的框架内以不断强化的合作生成共同身份。
整理:李念金牛股
天宇优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